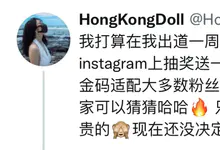「“至暗时刻”就是当代文青版的stand-up comedy。说的人笑着闹着,听的人听到一半不忍继续,发现喜的内核仍是好大一片悲。」
“科长你糊涂啊……”“这下文青滤镜碎了。”
这两天#贾樟柯 屏摄#上了热搜。起因是一个博主疑似在一场放映活动中看到导演贾樟柯举起手机拍摄正在放映中的《淘金记》电影画面,于是就发了一篇名为《亲眼目睹大导演屏摄》的小红书,其中提到“电影开始后整个片头贾樟柯都在屏摄”。
这在文艺青年和电影爱好者群体之间引起了巨大骚动,直到贾樟柯正式在微博上发表声明“全程没有拿出手机,更没有摄影”,舆论才得以平息。
(小红书原帖和贾樟柯的声明)
最近类似事件发生得不少,从舒淇、杨紫琼晒Labubu,到汤唯说“看了五遍《哪吒2》”还被拍到用“藕饼cp”手机壳,再到文淇给《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豆瓣打五星,都让那么同一群人感到“破防”,这些瞬间也都被列入了“文艺X的至暗时刻”榜单。
“至暗时刻”的背后,既有文艺逐渐“消逝”的年代人们对理想主义的怀疑,也是一个从文艺青年中逐渐分化出来的群体面对现实窘境时的自我解构。
01
贾樟柯屏摄风云:诬告理想的消亡
贾樟柯疑似屏摄之所以引起如此大关注,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时代印记,在大众尤其是文青群体中是权威性的存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到世纪交界之际,作为第六代导演之一的贾樟柯走进大众视野,他的镜头没有神话或史诗,没有浓重的爱恨交织,而是对准了一群身处社会边缘的底层工人、小镇青年、城市流民。
唱歌,行走,蹦迪,流浪,几乎构成了贾樟柯影像的大部分重量,他的作品也因此呈现出一种现实层面的裸视,简单地坚持着“非主流”,执着地要让小人物“说话”。
彼时也正好赶上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创作本身是理想化的,创作环境是简单甚至略有简陋的,创作的梦想也是纯粹的,而成为一个创作者,几乎是没什么硬性门槛的。那是一个“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不是说说而已的年代。

(彼时百花齐放的中国电影)
可屏摄风云发生的当下,高压环境之中,人们普遍地没有时间和力气去思考生存焦虑之外的事情,更谈何理想。
“一生都关键”的我们被长辈们劝说“不管你们未来是考公考编,还是考研……”,好像一切选择都要以实用性为优先导向,所有的经历和目标都可以被数据和等级量化,理想,成为了一种功利之外的轻浮的奢侈。
贾樟柯正是代表着一种稀有但坚实的“可能性”——在经济飞速发展、功利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他仍在拍无名者,拍失败者,拍时间和人性里最沉默的一角。这种朴素但有气节的理想主义在当代语境中显得突兀,甚至不合时宜。
在看到贾樟柯疑似屏摄的消息时,人们蜂拥而上,传播、造谣、甚至用着一些被极度压缩化的网络语言调侃“回头就给你发个微博”“有没有人‘出警’啊”,其实针对的不是贾樟柯本人,而是一种对理想主义的质疑,对理想消亡的“狂欢”。

(群聊中人们对贾樟柯疑似屏摄的讨论与“狂欢”)
《太阳照常升起》里有一句台词叫“你可以说你不懂,但不能说你没看见”。而如果理想裂了一个缝、开始坍塌,人们就可以假装它从未存在过。
就像网友们自嘲“早上还在叫贾樟柯‘老登’,看完《淘金记》开始称他科长,结果听说他屏摄因为电影原谅他的那颗心又要回去了”。“贾樟柯”只是一个符号,被人用之即弃,人们只是需要借他的疑似“塌房”来再次印证理想已死,聊以自慰般地让自己那些被放弃的理想们不再羞耻。
这不只是后真相意义上的一场闹剧,更是一种表浅的诬告和缄默于口的“敌意”。一群业已不再相信梦的人们,站在长时间寂寥无新事的太阳底下,“脑子一扔就是转发”,就这么诬告着理想的消亡。
02
从文艺青年到“文艺X”:无处容身的群体
在这次屏摄风云的背后,时刻follow事件发展动向,甚至将“贾樟柯疑似屏摄”与“汤唯是藕饼cp粉”“舒淇晒Labubu”一并列入“至暗时刻”榜单的,是这么一群从文艺青年中分化而来、自称“文艺X”的群体。
文艺青年最初诞生于互联网早期,他们对主流社会有距离感,但并不激进,更多是处于一种游离、漠视和“出走”的状态,比如开咖啡店、“逃离北上广”、去丽江听民谣住民宿。
而“至暗时刻”这个梗里的群体,是文艺青年更当下意义上的变体。他们有一些所谓的文化资本、独特品味和知识积累,却缺乏与之匹配的发展路径和“变现”渠道。可他们又无法接受对文艺的热爱和体察彻底沦为无用之物,止于私人化的自我品尝。
就像日剧《东京女子图鉴》中,女主角在面试时说自己的爱好是看电影,但对面的面试官一挑眉,说,“那就等于没有爱好呢。”这种类似的“审判”可能无数次拨弄过他们心里摇摆的天平。他们想反抗,想破解,想证明。

(《东京女子图鉴》)
文艺青年是“圈地自萌”的,但这个分化出来的群体选择走向公共空间,对外表达,进行自我展示,自我强化,自我重复。他们将自己的文艺属性和知识资本转化为了一类外在的“人设”,一股追求与众不同的戾气,一种适应了数字时代表达规律的自嘲和玩梗。
他们不断出现在互联网的表达空间,小红书上处处可见、随时更新的“至暗时刻”排行榜,细数着被他们奉为文艺男/女神的人“跌落神坛”的事件;徐佳莹、单依纯的演唱评论区中常出现类似“这完全是艺术啊,不懂的人只能听《跳楼机》”的评论;对小众文艺作品“好高级”和对大众文艺作品“土死了”的评价两极分化……
他们有些“看不起”大众文化,却又无法在主流社会中找到自己的安放之处,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无处容身的人。他们用外化的输出和攻击性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去对抗心底那点左右摇摆的,幽微的虚无。
03
“至暗时刻”:自我解构,直面窘迫
“至暗时刻”这个梗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击中了当下人们在理想和虚无之间的挣扎。
一方面,“文艺X”们仍在坚持那点儿理想主义,仍然会在同质化的浪潮中进行自我表达;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表达太边缘化,太不“主流”,太“脆弱”,他们不得不承认,甚至自嘲这些行为是脱离社会实际的,带点不合时宜的尴尬,带点主动暴露的羞耻,也带点太不合群的滑稽。他们用这种自我解构的方式保护着一小片自留之地。

(对典型“文艺X”群体的刻板印象)
这和脱口秀的内核很像。现代意义上的脱口秀兴起于20世纪初的美国,它最早是移民、边缘人和少数族裔的小天地,段子的内容也大多关乎贫穷,歧视,移民困境和文化认同。它从来不是强者的语言,它是“弱者”在失语中的自救,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武器。
“9·11”事件之后的几年,脱口秀大爆发,人们踩在创伤之上,讲的东西不再是传统的“setup-punchline”段子,而是带有一些自我揭露色彩的个人故事。演员们就这么大胆地把自我的恐惧、创伤和失败当成站在台上的谈资,对着来观演的人们进行人格“裸奔”,用玩笑掩饰崩坏的信仰。
就像近几年爆火的脱口秀节目里,小帕笑着说出“这个世界上不一定会有男人爱我,但是一定会有男人打我”,Echo说“害怕伤害父母,又害怕完全伤不到”,小蝶说“我的出生代表妈妈的绝育手术失败了”……

(一些脱口秀中“血肉疯长”的时刻)
这些让人笑出声的时刻却总有些“泪”的气质。你在笑她们的荒诞生活,失败经历和糟糕的原生家庭与亲密关系,但同时你也在认真倾听一个无法在主流环境中被认真对待的声音,你在尊重其用自我解构的形式为自己争取存在之正当性的行为。
“至暗时刻”就是当代文青版的stand-up comedy。这是一个安全出口,用以安放那些不可言说、无以名状的痛苦,说的人笑着闹着,听的人听到一半不忍继续,发现喜的内核仍是好大一片悲。
(图片素材来源于网络)